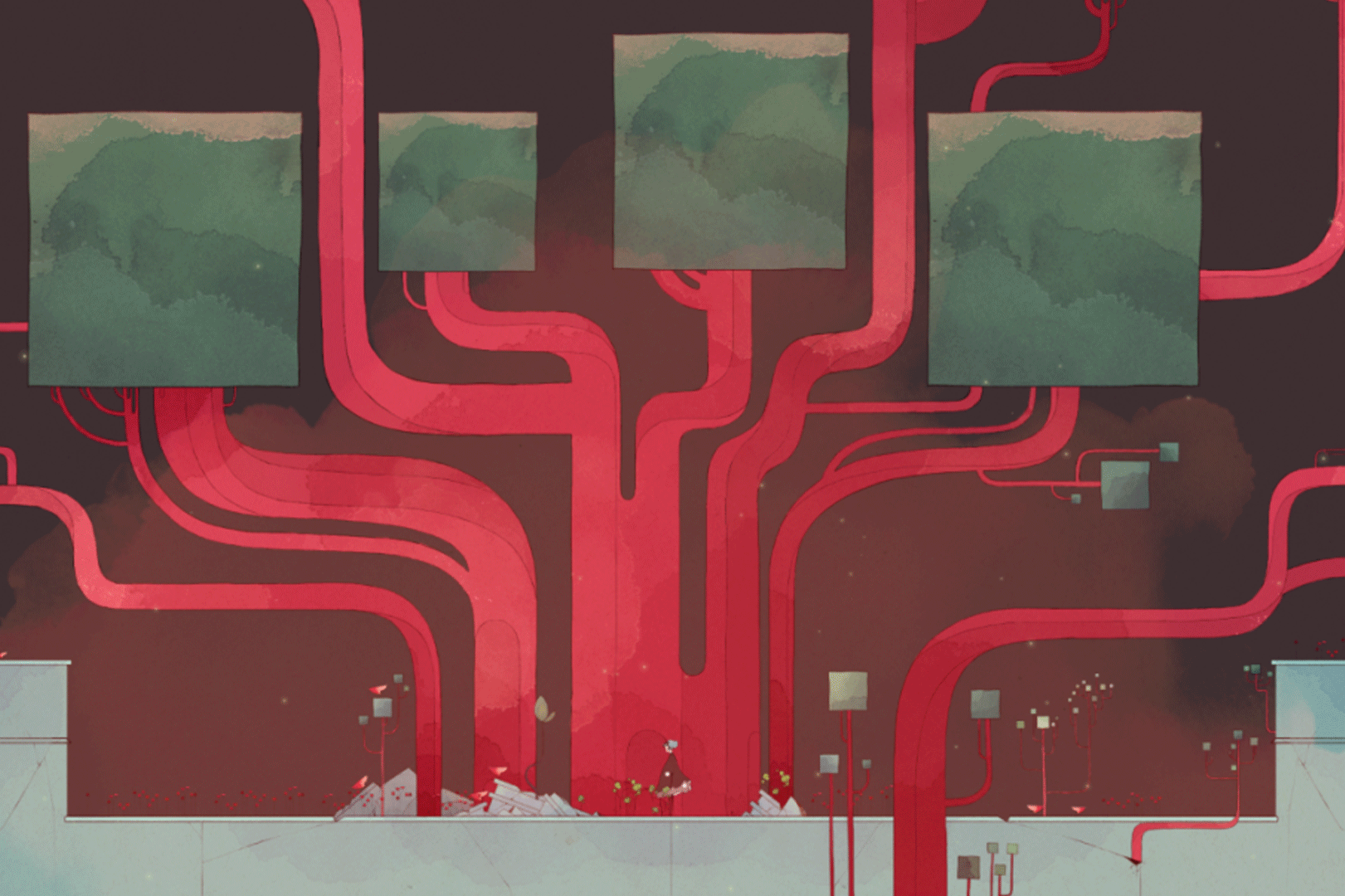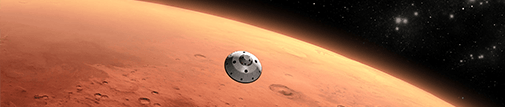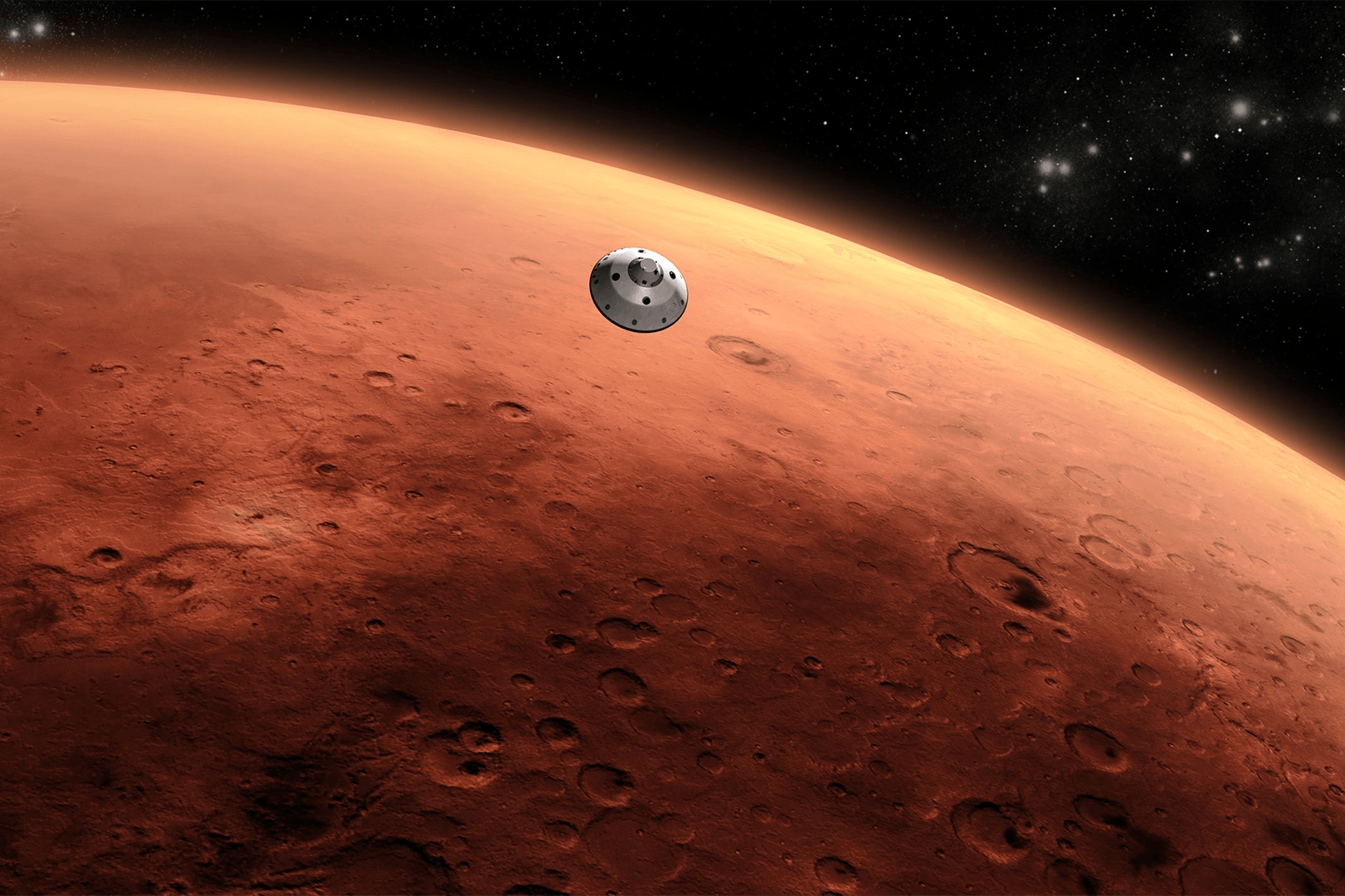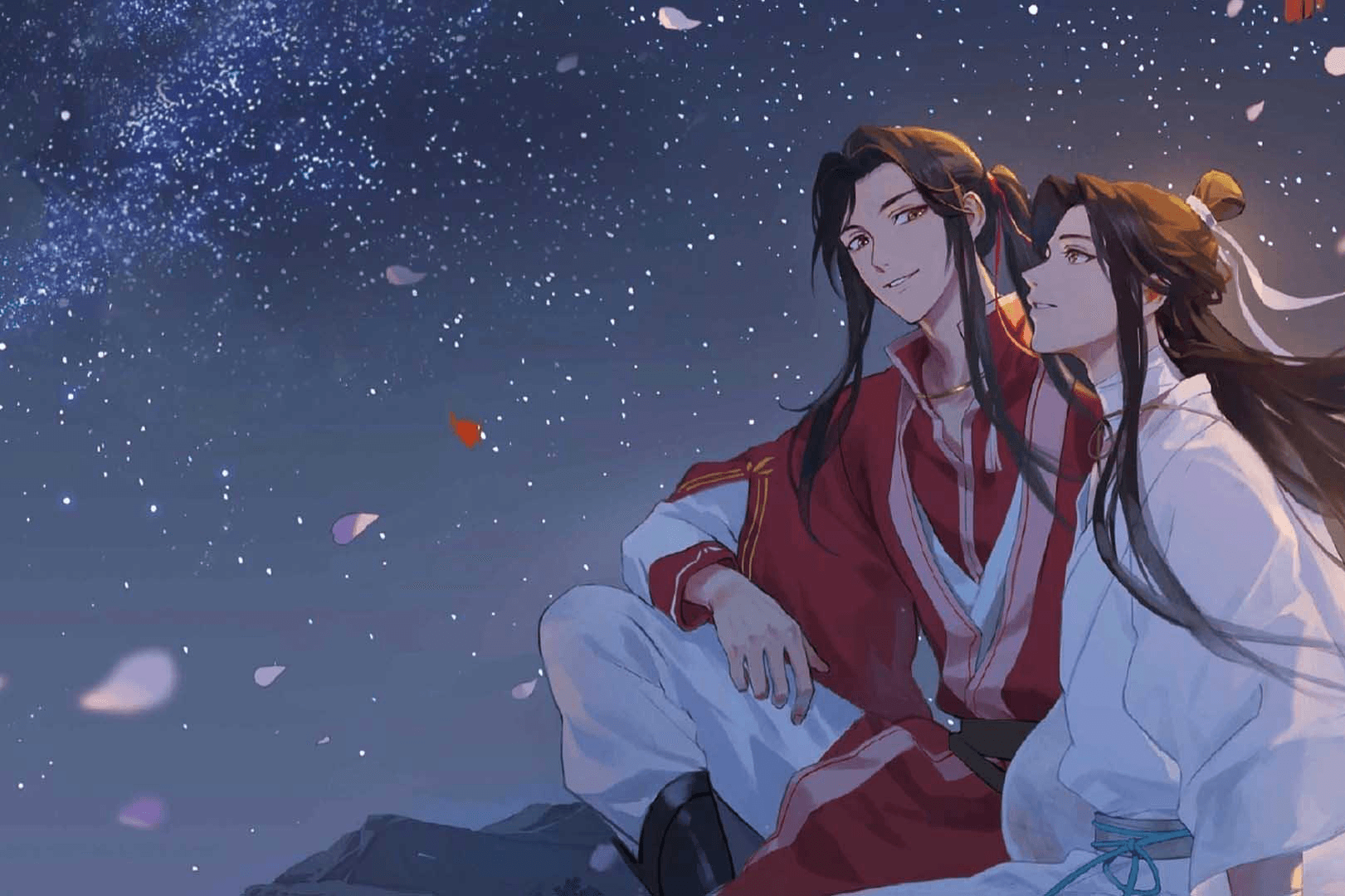如果昨天很冷,今天不是,那么现在理应是春天了。
无论是在这样的春天,还是在生命的余烬衰微的时候,我会想起,也只会再次想起,幽幽的溪水,玻璃,以及他的眼睛。
这天,像往常一样,我坐在离家不远的溪边,一块大石头上,扭头盯着岸边细小暗绿的草。这时节的草,像是不情愿的泥土的一部分,颜色和纹理都掺杂在一起。反射在我左脸和眼角上有些灼热的光斑突然消失了。我抬头,天突然阴沉了下来。低头,和缓的水流是暗色的,仍是看不清其间时刻变换形状的眼睛。
突然我意识到脚步声。就在我转身的同时,听到他的声音。“你的父亲是叫吴岐山吧?”
我站起来看着他。“是,你是谁?”
那人穿着灰黑色的长衫,像是唱戏的打扮,却又没有什么花哨的装饰,背着一个大的布包,但包里的东西并不重的样子。
“我应该是你弟弟,但我们不是同一个母亲。”我皱眉盯着他的眼睛,但他像是早就认识我,甚至没有丝毫要打量打量我的意图。
他说他被一个姓蔡的私塾先生带大,从未见过父亲,只知道父亲叫吴岐山。那个先生是父亲的朋友,本来只是暂为照顾他,但在他一岁多的时候父亲去闹革命,此后了无音信。他知道父亲有妻女,但不知自己的母亲是什么人。
“我对父亲也没什么印象。听母亲说他在我小的时候去修铁路,后来加入了什么四十九标,就再没回来。我从没听说过自己还有个弟弟,我今年十八,嗯,快十八,你多少岁?还有,你怎么找到我的?”他的眉毛跟我的很像,可能也跟父亲很像吧,而眼睛里有一种特别的透明感。
“我小你两岁。我找到你是因为梦,或者说是因为这半本书。”我更为不解。他从自己的包里摸出半本残破的书,给我看了眼封皮。我那时能识的字不多,只感觉封皮上有个字像是“游”,但不完全一样。他走过来坐到大石头上,书摊放在旁边,有一些密密麻麻但整齐的小字横向排着。我也挨着他坐下。
“我大概十岁的时候,有一次去山里玩,远远看到一群土匪抢劫过路的车马。我当时很怕,躲了很久,等到没有动静的时候,还是忍不住去那边看了看。有几具尸体横在路边,我一看到就想赶紧逃走,却瞅见一个闪闪发光的玻璃球在车子破碎的残片中,就壮着胆子过去了。我那时候还没见过玻璃,只觉得好看,就偷偷取走了。当时我正跟着蔡叔识字,看旁边有这半本书,于是顺道带走。”说着他从袖子里掏出一枚半个拳头大小的玻璃球,里面有一些玫红色树枝状的东西。“这里面是红珊瑚,一个当铺老板告诉我的。”“这就是珊瑚啊,我听说过。进城的时候,玻璃倒是见过的。”他把玻璃球递给我,我小心翼翼地从各个方向观察、抚摸,却没有发现一点残损与划痕。“我当时觉得这事并不光彩,没有给蔡叔看过这本书。后来我才意识到书上的字跟我们的文字不太一样,读的顺序也是横着从左到右。书本来就是半本,里面的字大多要连蒙带猜,读起来很困难。但我总觉得这书很有意思,偶尔会拿起来看看。直到前几年,一次梦中我忽然就意识到,这是游戏,书名也一定是《玻璃球游戏》。”
我偏过头笑着看他,朝他晃手里的玻璃球,用不太相信的眼神询问该是怎么个玩法。这是他第一次露出微微的笑容。之后每每我在夜里看到玻璃时,所见光芒幽微,总会想起这笑容。“不是这样玩玻璃球,是一种真正的游戏。啊,怎么讲?梦是很难形容的,我可以梦到,但讲不出来,倒是书里这种讲法是可以的,对,也只能这么讲,真是巧妙啊。总之这是梦的游戏,起码这半本书是梦的游戏。”他望着溪水,温风如酒,沉浸在自己的意识中禁不住地微微点头,因一只飞鸟掠过才朝我看来。见我茫然四顾略为失望,他继续吃力地补充,仿佛是在努力回忆自己的某些梦境。“梦里的玻璃球只是一种线索,真正的玻璃球游戏是一个精妙的体系,是庞大且伸缩自如的,整体来说似乎在不断地生长膨胀。梦里常见的碎片都是基本的元素,但是只有这些还不够,还要加上各种感官的反馈,有严谨的计算。梦里计算可真是太费力气了!美妙的声音是很重要的,还有……”“那梦里是有几个玻璃球呢?”我听不太懂,看着他又要开始沉溺在自言自语的想象中,就乱问一气。“这是什么问题……这……怎么回答?你看旁边这棵柳树,树上有很多很多的叶子,那能说它是‘一个’吗,可是又应该说是‘几个’?叶子还会生长,也可以被风吹落,真是难以回答啊。”“算了,算了。可你还没告诉我,这跟你怎么找到我有什么关系?”“嗯嗯,这就是了。我起先只是把这当做一种纯粹的游戏,算是夜晚的秘密。但是后来我发现在这个游戏中可以看到一些现实的片段!梦里看到实际发生的东西确实很自然,可如果是其他人经历过但自己没见过的事情,就很怪异了。而且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,还有尚未发生的事情。”“尚未发生?你是说预知未来?所以你知道我们会在这里交谈,对吗?”我几乎是大叫起来。“差不多吧,但不是能够清晰地看到未来的一切。看到的也只是碎片,梦里的那种碎片,都是不连贯的。有时候还会因为只看到局部而造成误解。”我当时惊讶极了,他这些话明明不可思议,我却总觉得像是自然而然的,有种抗拒不住的力量使我相信,可能是因为他的眼神,或是那个精致美丽的玻璃球。“我可以看到自己过去和未来的碎片,起先我试图竭力地逆着这种预见行事,但是往往在自以为避开的时候,还是会让那些景象出现。再加上那些景象总是扭曲的,只有真正出现的时候,我才恍然大悟。”我拿起那半本书翻来翻去,封皮是淡淡的绿色,残缺且满是褶皱。书只剩下前半本了,起码丢了一个封底,但是看最后一页并不像写完的样子。我本就识字不多,书中又小又密的文字也略为怪异,实在看不出什么门道。“所以你是在看到自己未来的时候,看到我了吗?”“是,我看到了你,而且不知怎的,我猜到你可能就是我那个未曾谋面的姐姐。我还看到我沿着这条小溪行路的一些记忆,啊,应该可以叫记忆吧。一年前蔡叔的大哥来拜访,蔡叔想一同离开,去近海的地方。而我选择了留下,也是想找到你,或者说验证这个猜想。其实我们住的地方不太远,从这里一直往北走的话,大概走五天就可以,只是我并不知道,兜兜转转了近一年。”
云层渐渐褪去,日光再次灼热起来。“父亲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,难怪你找起来这么困难。这一年,你是怎么过来的?”“哈哈,你该是可以猜到的。”他笑了,顿了顿,只是我没有要猜的意思。“我既然能看到一点未来的事,就可以给人算命。过去的事和未来的事,往往我也分不太清,就掺着说,这样反倒效果不错。你看我这包里,一堆这种东西,用来故弄玄虚罢了。不过算命这行当,糊口确实还是可以的。”他翻开包给我看,果然有一些罗盘、竹签之类,还有不多的钱和干粮,再加几件旧衣服。“那你能知道我未来的事情吗?”“按道理是可以的,不过我只能在见过你之后才能看到那些事,说不定今晚如果做梦可以试试。不过,我现在做梦越来越少了。我不知道原因,可能是书不完整的缘故?”我点点头,很盼着他能说出些关于我未来的事情。“哦,那你住哪里?要不在我家住一段时间吧?”“不必了,我要走了。”他转头向路的尽头看去。“你这就走了吗,你要去哪,我该怎么找你?”他转过头来望着我,“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,但是我该走了。”这时我知道,无须挽留,也无法挽留。
他起身,在石头上重新装好自己的包裹,很是仔细。“你这就走了。我才刚刚见到自己的弟弟。”我低头看着他装东西的侧影,小声说着。“啊,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”“他原来给我起名吴昭,不过从我开始四处流浪之后,我就叫自己‘格拉斯’了。听说‘格拉斯’是玻璃的英文,这书的作者似乎就叫格拉斯。”他装好了其他的东西,背上包,把书递给我,“书和玻璃球送你吧。”“你不是要靠这个算命谋生吗,我怎么能拿?”“无妨,我不知看过多少遍了。”我接过来,一手攥着一物,怔怔地站在原地,目送他的身影在转过山后消失不见,竟没想过要送他一程。
这就是那天的事,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,在我能够复现玻璃球游戏之后,这是我能在梦中看到的最清晰的记忆。我见过很多他过去破碎的经历,但是我从未看到他在转过那座山之后的故事,也再未见过他,或是听说过一个叫格拉斯的人。
现在我奄奄一息,不用费力地睁开眼睛就知道,床边我可怜的才刚刚十岁的儿子已经带着泪痕睡去了。但我见过他长大后的笑容,也是带着像玻璃一样透明的颤动。
男孩在醒来后发现母亲的身体已经变得冰凉且僵硬,他大哭着,惊恐趔趄地跑出去叫人,还绊了一跤。
几天后这间简陋的屋子再次空荡静寂起来,只是床上也空空荡荡。男孩坐在床边,在光线黯淡的墙角看到一个翻倒的小箱子。他记得母亲偶尔会打开看看,但总是放在高处不让乱碰。有一次他执意去抢,母亲便从里面拿出那个漂亮的玻璃球,但是玩一会也就腻了。
他走过去捧起破旧的小木箱子,箱盖变形,打开有些费劲。拿出那个玻璃球,红色的珊瑚鲜艳如旧,但玻璃球的边缘却泛着幽微的绿光。这时他才发现,箱子底下还有半本书,残破到仿佛一碰就要化为齑粉的封面上横写着五个字,但他不认识。翻开封面,其余的书页光洁如新,空无一字,只是隐隐透着淡绿,如同玻璃球一般。